天逐渐黑了,似乎要下雨,云厚得好象要掉下来。 我把皮箱放在因湿润而很柔软的地上,歇了歇。几茎草从土缝里挤出来,表舅家应该不远了。 由于严重的神经虚弱,医生告诉我必须静养一个时期。因此我想去表舅家住上一个月。据医生的说法,山水可以让我的神经回复。 谁人小村子,在我的影象中不象个真实的,然而母亲告诉我,我是在那儿出生,长到了三岁时才走。可我却记不得什么了,只记得一幢大院里来往复去的人,以及一些粗笨而老旧的家具。若是不是母亲给我的地址,我都不知道这个浙北的小村子在什么地方。 那是个春暮的黄昏。在一带隐约的山影间,雾气弥漫。天已暗下来了,在那些雾气尚未合拢时,我瞥见了在山脚下的一幢十分古旧的修建。我不由感应一阵欣慰——终于,我赶在天黑以前来到表舅家了。 走到这幢旧屋前,我才发现那些伟大的参照物给我了一个何等错误的印象,在远处看来,这屋子只不外古旧而已,掩映在树影里,还显得有点小巧玲珑。但走到跟前,我才发现光一扇门就足有五米高,那两扇门是用厚厚的山木做的,上面包着一层铁皮,钉着铜钉。年久失修,铁皮已多数已锈了,有些地方甚至已烂出了洞,露出下面的木头。铜钉也已经昏暗发绿,只是门上那两个熟铜门环,约莫经常有人摸,倒是光润发亮。 门是用十分粗大的青石砌成的,双方的石条上刻了副对联,一边是“向阳花木春长在”,另一边是“积善人家庆有余”。很熟滥的联语,倒和这屋子的名目很合适。 我走到门边,捉住门环。一股冰凉直沁心底,倒象是摸到了一块冰。我敲敲门,内里有人应了一声:“来了来了。”接着是有人趿着鞋走出来的声音。趁这时机,我转头看看烟雾缭绕的暮色。不知为什么,我突然感应一阵恐慌,似乎突如其来的一阵寒流捉住了我。 那儿有些什么? 我正凝思远望那一带树林,门“呀”一声,开了。 开门的是我表舅。 我只在很小的时刻看到过表舅一面。那是我五岁时,我的曾外祖母过世,散在天下的上百个亲戚都赶回来奔丧,我第一次知道国家有那么大。而我对这幢屋子的影象,也多数只局限于这一天,在印象中,来往复去的那些亲戚全是些不折不扣的生疏人,那时的表舅,也有点风神俊朗的意思。 现在,他看上去显得有六十多岁了,按他的岁数,该是只有五十二岁。我刚要启齿语言,他说:“进来吧,我接到表姐的信了。” 我拎起包,走了进去。也许是由于黄昏了,内里显得很幽深,迎面是堵影壁,壁绘却早已模糊不清。绕过影壁,当中是个院子,大门是朝南的,北墙上爬满了爬山虎,墙根种了几本剪秋萝,开着几朵花。北墙的西角上,有间柴房。院子双方是两层的青砖房。中国式修建,向来考究对称,双方也造得一模一样。而大门双方,也是两层的青砖房,我还记得,那是当厨房用的客厅——不知道表舅另有没有客来了。 “我给你放置了一间房了,楼上朝东的,楼下潮得很。” 表舅闩好门,领我上门去。 沿着仄仄的楼梯,我走上楼。突然,从拐角处探出一个蓬头的脑壳来,我吓了一跳,表舅说:“二宝,来见见你表哥,你还没见过他。” 我说:“是表弟么?”有这么个蓬头垢面的表弟,着实让我以为不恬静。谁人二宝大着舌头说:“我是女的。” 果真,她穿着一件花布夹袄。只管她头发蓬乱,我我瞥见她的脸上、手上和衣服都很清洁。她的脸上,堆满了弱智人的傻笑。表舅说:“叫表哥,别这么没礼貌。” 二宝看着我,说:“表哥。”吃吃一笑,跑上楼去。表舅摇摇头,说:“这孩子,有点缺心眼,还算听话。唉,那时这屋里全是人,长房二房,大巨细小足有二十几口,现在只剩下我一家三口了。看,你妈小时刻从这儿掉下去过。”他指着楼上过道里的一角破损了的扶手。这楼并不高,只有三米左右,由于楼下原本就不住人的吧。院子里又是泥地,摔下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只是,我想到了我唯一记得的昔时谁人这幢房里挤满了人的出殡排场,也比现在更有些人气。 我叹了口吻,说:“表弟怎么不见?” “大宝在镇上开了个小店,不常回家的。过几天让二宝带你去看看,你还跟他打过一架呢。到了,你的房就在那头。” 他领我到边上的一间屋子。一推门,内里黑压压的,他拉着了电灯,险些同时,过道里响起了一阵噪杂的音乐,接着,一个男子的声音响了起来:“╳╳乡人民广播站,现在最先广播。” 房里,器械很少,一张床靠在屋角,由于灰尘太大,蚊帐上遮着已经变黄了的的塑料纸。表舅说:“热水在楼下灶间里,要就自己去拿。路上辛勤了,早点洗洗睡吧。”他转身出去了。 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,听着广播里发出的稀里糊涂的声音,如一阵凉水逐渐浸透了我的全身。模糊中,我似乎来到隔世。 和衣躺在床上,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模糊的声音。静下心来,就听得出那是个广播剧,不知何时录下来的,也许,在这个偏僻的乡里,有个家伙正在一间广播站里摆弄几张古旧的密纹唱片吧。那些时断时续的声音象从水底冒上来的一样,一会儿是个女人带着哭腔说:“你骗了我,我太傻了。”过一会儿又是一个男子的声音说:“人生原本云云。”原来这两句话一定不是在一块儿的,放到了一起,倒有种新鲜的意味,好象是谁人广播员有意为之一样。 我想到了许多年前,在这大屋子里的那一次出殡。许多人围在一起,我的曾外祖母躺在一张竹榻上,脚边点了一枝白蜡烛。人们的声音此起彼伏,在头顶蠕动。 在人群中,我依稀记得一张脸。 这是个女人。 一个极为优美的女人。 一个五岁孩子心目中的优玉人人是什么样的?我固然忘了。然则厥后我回忆起这一情景时,我才发现了她的优美让我记得很深,我才气清晰地记得她的每一个特点。 她穿着白色的对襟夹袄,头发黝黑发亮,以至于厥后我读野史时,读到陈叔宝的宠妃张丽华“发可鉴人”时,才发现昔人的考察力着实惊人,这几个字着实极好地说明晰那一头如水的长发。而她的脸在我的影象中却白的吓人,我嫌疑是不是我的影象诱骗了我,以至于她的神色在我影象中越来越白,白得象汉白玉雕出来的一样没一点血色。 我一直不知道她是什么人。那时,她约莫有二十三、四岁,神情并不很悲痛,可能是哪一支的舅妈吧。我记得我看到她的脸时,就吓得垂下头,不敢多看。然而,在我的心里深处,总象有种诱惑,好象我一定要看。而每看一眼,我都记得我人心惶遽,说不明了的恐惧。 她的脸也许给我的印象是太白了,让我已记不清她的五官。我只是以为,她更类似于那些古老壁画中已经剥落殆尽,而只能看得见一点轮廓的仙女。但已经漫漶了,那仙女与妖魔也没什么区别。 我点着了一支烟,深深吸了一口。窗外,夜色渐浓,广播时传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幽渺,换成了一个女人咿咿呀呀地唱一支地方小曲。原本这地方的方言就很费解,声音又模糊,加上是唱出来的,更是不能辨了。在夹杂着电流噪声的曲调里,依稀只以为一种苍凉。夜色如水,一个女人独自穿了破衣服,在桥头上低唱那种感受。再热闹的调子,也只会让人以为凄楚。 抽完了烟,我把烟头扔进床下的一个破瓶子里,从包里取出了洗漱用具,走出门去。下楼时,在拐角处,一股湿冷的气息直扑过来。 灶间里,用的照样灶头。也许是由于煤欠好运吧,价钱又贵,不象柴草,满山都是。灶眼上,一锅水搁在上面,灶膛里另有焚烧,水还很热。我用铜勺舀了一杯水,走到灶间门口的水沟前,最先刷牙。 我把一口水吐在地上。不知为什么,背上一阵冷,不由打了个寒噤。楼上,广播还在响,那女子拉长了调门,拖出一个长音。不外也许是唱片跳纹了,人的一口吻绝不会这样长法。并没有风,楼上的灯光映在地上,照出了一方亮。可地是泥地,以是这一块亮不外比边上的颜色淡一点而已。 我又垂下头,去刷牙了,可我心里,却隐约有种不安。若是不是我眼花,那适才一定有个影子很快地在楼上掠过。我虽然看不到楼上,那地上投下了栏杆的影子。 这是表舅照样二宝?或者是只野猫,由于我没见表舅家里养猫。我胡乱预测着,但心底总有点不安。也许,这是我的神经虚弱引起的,我总是把一点风吹草动都想象成荒唐不经的事。 我洗着脚,吃力地识别着楼上传来的不清晰的广播声。当我洗完脚,出去倒水时,那里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,我只听清了最后的两个字是“竣事”。 站在楼下的走廊里,看着灯光。一切都平静,但我信托还不到九点,只是在山脚下天黑得早,周围还没人家,以是显得很晚了。 洗漱完了,我搁好脸盆,走上楼去。走过那幽暗的拐角时,突然又从心底升起一阵恐惧。我向后看看,死后,是楼下那走廊,很幽暗。我以为那儿好象有什么器械让我畏惧,可又引诱着我前往。我屏住呼吸。脚繁重得象灌了铅,却总象是情不自禁地想走下楼去。 不要走下去。不要走下去。在心里深处,我对自己说。但楼下的那一片漆黑,似乎有种妖异的气力在蛊惑着我。 “有人吗?” 我战战兢兢向楼下说着,我的脚已经迈下了一级楼梯。 “是你么?” 我闻声表舅在楼上说。他趿着鞋,从上面走下来。 “没什么,我刚刷完牙呢。” 他说:“那早点睡吧。”他走过我,下了楼。我走到楼上,瞥见他站在北墙根处小便。 走过他的房间时,突然,我又有种突如其来的恐惧。他的房门虚掩着,没开灯。二宝也许和他睡一间房的吧。我逃也似地回到自己房里,直到躺到床上,我还听获得自己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。 第二天,我起得很晚。穿好衣服,走下楼,瞥见表舅在磨一把锄头。他头也没抬,说:“起来了?粥在锅里,随便吃吧。” 我准许了一声,去弄点水洗漱。表舅磨锄头的声音“嘶啦嘶啦”的,前一声短,后一声较长。可能是那块磨刀石已磨成了半月形,厚度差异,声音也差异了。 我洗漱完了,出来时,表舅正把锄头装到把上,准备出门了。我说:“表舅,你要下田吗?” “是啊,田里都板了,要翻一翻。” “我也去吧。” 表舅看了我一眼,道:“你行么?” 我弯弯手臂,看看自己不算太难看的肌肉,说:“农活我不行,可气力另有点,给你打个下手总行。” “你不去镇上了?” 我想说镇上也没什么悦目,与其走上十几里路去镇上,不如干点家活。我嘴上却说:“明天再去吧。” 表舅说:“那你去吃粥吧,我再磨把锄头。” 粥是白米煮的,很是香甜,下粥的却是些腌辣椒。我基本吃不惯这么辣的器械,只咬了一小根,就把两大碗粥都喝下去了。 吃完了,表舅已经磨好了锄头,他给了我一把,我扛着跟在他死后出门。在大门口,表舅扭头喊着:“二宝,不要乱跑,闩好门。” 走出不多远,不知为什么,我转头看了看。我瞥见二宝站在门口,盯着我看。若是不是我的幻觉,我发现她的眼亮得吓人, 表舅家的田离宅子有一段路。到了地里,看到田里的土都已经干结了。表舅在最先在田里挖一条沟,把土翻个个。我挖了没几畦,只觉手臂象断了一样,锄头也举不起来,落在表舅死后好大一截。 表舅闷着头掘土,好象什么也不体贴。我看看天,天上黑云渐浓,看样子要下雨了。 我说:“表舅,天快下雨了。” 他停下锄头,看看天,道:“是啊,过不了一个钟头就要下了。你帮我回家拿个斗笠跟蓑衣来,今天要把田翻好。” 我也着实有点不想干了,就扛着锄头回去。回到表舅家的大门口时,乌云已经很浓了,天暗如黄昏,转头望去,倒似暮色降临。说也新鲜,走过来时路上没没见若干树,但看已往,树却密密麻麻的。 我推开厚重的门,把锄头放在过道上,表舅的蓑衣挂在灶间门外,可是只有一套。我想再找一套,万一回来时下雨了好穿。只是这儿没有了,我想问问二宝,可不知她上哪儿去了,再说问她也未必能问出些什么来。 我走到柴房门口,从窗子里向里看了看。很幸运,内里的柱子上,正挂着一件蓑衣。我走了进去,拿下了那件蓑衣。这件蓑衣是用细竹丝编成框架,上面铺着箬叶,也就是裹粽子那种。很新鲜,箬叶上,有不少被划破的地方,却并不象穿破了的。 我刚想走出去,猛地瞥见在那堆柴禾后面,另有一扇小门。门上,挂着一把开了的大锁。是个废弃了的后门吧?后面也许有个院子? 我推开了门。 门一推开,就象一阵潮水汹涌而至,我吃了一惊。内里,象燃烧一样,开满了蔷薇。 只是春暮,虽然蔷薇四序能着花,但这院子里太多了。蔷薇本就是有点象爬藤植物,种着就会爬满整幢墙,而这里,简直是充满了整个空间,四处都是。这里的蔷薇大多是艳红色,只有少数是白的或黄的,绝大多数都是大朵,夹杂着少量十姐妹一类的小朵蔷薇。这儿的花开个那么狂野,只能用“妖艳”来形容。 在蔷薇丛中,有一条狭窄的小道。有这么一条路,多数是有人经常走动,否则早就被长势极快的蔷薇淹没了。我披上蓑衣,向里走去。这时,我才想到,蓑衣上划破的痕迹也许都是这么造成的吧?那会是谁呢? 我沿着小道走着。路十分难走,不时有细刺勾住我,若是不披这蓑衣,我只怕早就转动不得了。蔷薇的刺许多,但没什么香味。这么多花在一起,本该有极浓的香味才对。古书上不是说,韩愈接到柳宗元信后都是先以蔷薇露盥手后开阅?也许,这里的蔷薇都是无香的吧。不知为什么,走在这些花丛中,总让我有种荒唐的感受。 路弯弯曲曲。这园子应该并不太大,可也许这小道太多曲折了,走了半天也走不到头,而且也不能走快,正让我有了一点迷失的惊慌时,我瞥见在前边的花丛里有一间小屋。 这小屋掩映在花丛里,可望而不能及。要直走已往,只怕要用刀子打出一条路来。但我以为总该有一条路通到那儿,就沿着这路拐来拐去。由于有了个目的,以是这么乱转也不是太无聊。 不知走了多久,我终于看到前面就是那小屋子了。我长吁了一口吻。 这是间很小的木屋。若是是砖砌的,外面抹上石灰,我可能会嫌疑那是座江南墟落里前些年常见的宅兆。那时一些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总是把祖先的宅兆做得象一间小屋子。但这间小木屋有一扇窗,一扇门,一定不会是宅兆。窗上爬满了蔷薇,只怕内里一点光也透不进去吧。门上倒没有缠着蔷薇枝,但我看获得周围的枝条上有折断的痕迹。 这门是向外开的,但由于外面都是蔷薇枝,拉开来会很艰辛。我刚扯开几枝长得过于靠近门的枝条,正要拉门,门却“呀”一声开了。 我吓了一跳。但马上看清,内里出来的谁人披着蓑衣的人是二宝! 她瞥见我,象见鬼一样,叫道:“不要进去,不要进去!欠好进去的” 她象一张划坏了的唱片一样那么翻来覆去地叫着。我道:“二宝,内里有什么?” 二宝说:“是妈妈。她说欠好有人的。” 她的话让我一阵发毛。表舅的妻子在十几年宿世二宝时死了,这我早就知道。岂非内里是个死人么?可二宝却说什么“她说”,二宝不太象会说谎的人,可内里真会有人? 二宝已经闩好了门,回过头来对我说:“表哥,你欠好说的。你要跟爸爸说了,爸爸会杀了你,你欠好说的。” 她一边反频频复地说着,一边从地上的草丛里摸出一把大锁锁上门,也许很怕表舅会打她。看来,她虽然弱智,但说谎照样会的,只是不知道哪些谣言可以骗人,哪些骗不了人。我看着她嘴里说出那些可笑的话,还笨手笨脚地锁门,却不要我帮,不由有点可笑。她锁好门,又嘱咐我一句:“欠好告诉爸爸的,噢。” 在这一瞬,我才发现二宝实在可以算得上是个尤物。只管她一身的邋遢样彻彻底底地损坏了她的仙颜,但从她的脸型,还可以看出,她该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惋惜了,我想,但马上又以为,在表舅家里,她是个弱智不见得是件坏事。 我沿着小路出来,二宝在后面拼命地推着我,象是在赶我出去。身边,繁花似锦,乌云也不知在什么时刻散去了,阳光象水一样直泻而下。不知为什么,我只以为周围那么妖异。 给表舅送去蓑衣再回来,过了不久,果真下雨了。这场雨直下到黄昏还未曾止,天也冷了许多。吃过晚饭,我半躺在床上,抽着烟,听着风雨声中传来的有线广播的声音,只以为心头发冷。 风大了。窗外,雨打得地上起了一层水雾,时而有风带着风点雨吹进房来,靠窗的楼板上也湿了一块。我起身,扔掉烟头,关上了木板窗,登时,窗上“沙沙沙”地响过一阵,这让人心头更觉阴冷。我翻出一本书,那是本历朝七绝选,当我还未曾得神经虚弱时常读上两首,看成催眠的药剂。由于时常翻几页,有不少诗我都已经能背下来了。 我随手掀开一页,是一首清人的作品:“依然被底有余温,尚恐轻寒易中人。最是梦回呼不应,灯昏月落共凄神。”写得并不怎么好,问题是《江上》,却没有扣紧问题,有点莫名其妙。然而,不知为什么,这首诗也让我以为身上越来越阴冷,好象伤风了。 我正妙想天开着,不知不觉打了个盹。醒来时,书扔在了地上,天色已暗了。我拣起书,这时,我突然听到了一阵细细的哭声。 这是个女人! 是二宝么? 我马上就知道这不太可能。二宝的样子,似乎不会这样哭法的。这哭声幽咽凄楚,在风雨中象一缕游丝,时断时续。 我站起身,拖着鞋走到门口。过道里暗得恐怖,这哭声似乎也不象从隔邻传来的。由于还在下雨,在雨声中听来,无比的幽渺,让人心头情不自禁地一阵阵冷,听不出是从那里来的。 也许是什么声音,我听岔了吧? 我看着院子里。院墙很高,后面谁人园子也看不见。这么一声雨,会打落不少花朵的吧。我想着,点着了一枝烟。就在点烟的那一刻,我突然瞥见了一张雪白的脸! 这张脸在我点烟时正仰面向上瞧,若是不是在点烟时眼光向下瞟了一眼,基本不会注重。我吃了一惊,手一松,烟也掉了。我只觉背上向爬过一只小虫子,全身凉得发痒,甚至,连我的心跳也一下子听获得了。 我扑到栏杆上,掉臂会掉下去的危险,向下看去。可恨的是,下面着实太黑了,象一个深不能测的深潭,什么也看不清,但我感应有一个影子极快地闪过,无声无息。我叫道:“是谁?” 没人回覆我。我正想跑下去,只以为有人捉住我的手腕。我吓了一大跳,转头一看,是表舅。 “下面有人!” “别去。”他说。他的脸也白得吓人,不带点血色。他只穿了件单衣,看样子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。 “下面有小偷。” 表舅照样抓着我,他小声说:“没有人的,别去。看,二宝也哭了。” 这个理由并没有说服力。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,似乎,他知道下面有人的。也许,是他情人吧,不是名正言顺那种。我有点自作伶俐地想。 楼下,暗得没有一点活气,空气也象要结冰。 不知不觉,在表舅家住了一个星期了。 我是看到自己带日历的石英表时才知道这一点的,表舅家没有日历,真有点“山中无历日,寒尽不知年”的味道。 这一个星期里,我有时干点家活,有时就躺在床上看书吸烟,要不就做点饭菜。书快让我翻烂了,也快全背下来了,只是谁人蔷薇园更让我好奇。表舅虽然不在家,二宝却整天随着我,似乎怕我再去。表舅说过要让二宝带我去镇上看看大宝,却一直也没提及。那镇上治安不太好,我来的那天就听人说一大早有个小贩跟流氓起了冲突,被流氓杀了,表舅也许不想让二宝去那地方吧,而我又不熟悉大宝。 这一天天阴森沉的,中中午还阴得象黄昏。我翻着那本诗集,模模糊糊中,又看到了那两句“最是梦回呼不应,灯昏月落共凄神。”也许是我的神经虚弱又犯了,心里抑郁得不行,总以为象有什么事会发生。 吃过午饭,表舅又扛着锄头下地去了,二宝在楼下玩着一坨泥巴,不进斜着眼看看坐在楼下廊里看书我的,也许怕我会偷偷去谁人蔷薇园吧。若是我没有好奇心的话,这是十分镇静和无聊的一天。我无聊地翻着书,然而,我着实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。那间潜匿在花丛中的小木屋里,事实有什么器械?若是没有二宝,我一定会跑去看的,就算没蓑衣也一样——纵然会被刺刺得全身是血。可二宝虽然弱智,却很执着,认准了什么,一定也不放松,就算我上茅房她都市在门外等着。 我放下书,看着那堵盖住园子的墙,想象着许多年前的事。这幢屋子原本并就是我家的,听说我家原本也算个有点资产的小田主,厥后人口众多,而几个曾叔祖又染上了乌烟瘾,十几亩地都卖光了,只剩这宅子是祖业,祖训不得出卖。以是厥后闹农会时我家成了有宅院的下中农,很成为笑谈。 那堵围墙把后面的园子遮得严严实实的,一点也看不到。最早时的祖先为什么把墙筑得这么高?固然,那时这儿不太太平,我小时刻还听外祖母说过闹长毛时的事——固然,那些她也是听来的。这里地广人稀,周遭十里周遭就这一幢院子,固然要把墙修得高点厚点吧。 突然,我有一个十分恐怖的想法。在那屋里,会不会是个死人呢?二宝说是她妈妈,可她妈妈早死了,生她时难产死的。 我走下楼,二宝还在起劲地玩着泥巴。那些坨泥巴被她又拍又打,不成个样子。我喊了声:“二宝。”她抬起头,看着我,两只手还抓着泥,我说:“二宝,去镇上要若干时间?” 她想了半天,说:“吃好饭去,回来用饭。” 只管语法不通,但我也知道,带她去镇上,一个下昼是不够的,除非能搭个车。可这儿的路也只是条走出来的小道。拖沓机也不外一辆。 我看了看柴房的门。门没关,不知内里那扇门开着没有。我走到内里,那扇门上挂了一把大锁。看样子,那天表舅是凑巧忘了锁门吧,由于我那天见二宝出来时也没锁这扇门。 我弯下腰,从门缝里向里张了张。内里依然繁花似锦,那些如火如荼的蔷薇险些似是燃烧一样在怒放。蔷薇是种花期很长的植物,听说在广东、云南那一带,可以一年四序不停。这院子里的蔷薇并没有人照料,虽然长得很乱,却也长得出奇得好。 我直起腰,一转身,却差点撞到二宝。她偷偷摸摸地站在我死后,两手也脏得象泥捏的。这让我又好气又可笑,我说:“二宝,你去内里,你爸爸知道么?” 我原本只是随口说说,谁知她的脸一下煞白,道:“不要!不要!不要告诉爸爸!”一边喊着,一边向退却去。她的反映太大了,让我新鲜。 我说:“二宝,你告诉我那屋子里有什么,我就不告诉你爸爸。” 她看着我,呆了片刻,咬了咬嘴唇,才道:“那你欠好告诉爸爸的。”我点颔首,说:“固然。”她伸脱手来,道:“拉个钩。” 她刚玩过泥巴,一只手肮脏之极。但我的手指勾住她的手指时,只觉她的皮肤滑腻柔腻。她的面相原本就很美,手形也很悦目,只是头发蓬乱,手上也太脏了。这时却看不出她是个弱智,我心中忍不住一阵叹息。 二宝拉了拉我的手指,也许断定我不会说了,道:“内里有饼。” 有饼?我不觉怔了怔,原本以为有什么震天动地的隐秘,这时不由大笑起来。二宝显然不明了我为什么要笑,呆呆地看着我。 笑了半天,我突然想到,谁人屋里有饼的话,意味着什么? 天很阴森,气温并不太低,我的身上却一阵发冷。 表舅一样平常是六点回来。五半,我烧好了饭菜,给二宝洗能手,等着表舅回来,只听得表舅在大门口高声叫着我的名字,说是大宝回家了。 大宝和我同岁,比我小几个月。听表舅说,小时刻我还和他打过架,可我一点也不记得了,连他的样子也一点也没印象。若是算一下,我和他也有二十来年没见了吧。我走出灶间,表舅把锄头靠在墙角,他死后随着一小我私人。黄昏了,天色很暗,有块影壁挡着,更看清面目了。 我伸脱手去,说:“大宝么?” 他也伸过手来,说:“表哥啊,住得好么?我生意忙,一直没回来。” 他衣服很单薄吧,手也冰凉,我说:“没用饭吧,快去吃点,菜还热的。” 我们围着桌子坐好了。菜并不算好,我炒了点腊肉,一点蒜苔,再是点青菜汤,都是表舅从菜地里拔来的,很新鲜,住了这些天,我的掌勺手艺大进,到底没几小我私人能这么天天吃到脱离土壤才十几分钟的菜的。 吃完了饭,表舅提着碗去井台洗碗,让二宝陪陪我。天色暗了,快到清明,云厚厚地全是雨意。大宝把腿搁在条凳上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。我摸出一枝烟,他接过来,我打着了火机给他点着。他的神色不太好,做生意也太辛勤吧。他抽了口烟,说:“表哥,没什么事,多住几天再走吧。” “住也有一星期了。大宝,你生意还好么?” “也就挑点杂货卖卖,赚点辛勤铜钿用用。” “那你的货扔那儿没关系么?” 他吐了长长一条烟柱,说:“没关系的,跟那儿一个馆子里说好了,在他们柴房里搁一搁。再说,也没什么值钱的器械,就是点骗骗小孩的玩意。生意难做啊,税还重,你也知道的。你做什么?” 我苦笑了一下。由于严重的神经虚弱,我早已辞去了事情,现在是坐吃山空了。但我没有告诉他。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,可没见大宝,表舅说一大早他就走了,馆子里客多,器械欠好放得太久的。我伸了伸懒腰,想着,在这个大院子里,一切都象和现实脱节了,只有大宝另有点着实的气息。他一走,这院子又笼罩着一层诡秘。 也许是我多疑,但我总以为这一切都云云地难以捉摸,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。可能是我的神经虚弱又犯了,每一回犯神经虚弱都云云,失眠,多疑,这一点我很清晰。在我照样个孩子时,我就总在嫌疑门外有不能知的异兽,只管打开门就可以看个清晰,可那时我就缺乏那种勇气。 我坐在窗前。早上雾气很大,表舅扛着锄头又出门了,我最先抽一根有点发霉的烟。天最先下雨,雨下得窗台上湿成一片,而我不想关窗。不是玻璃的,一关窗,这屋子马上就暗下来,好象一下子就沉入深夜。只有一点光线能给我一点暖意。 我抽着烟。窗台上,砖缝里有一根长长的细草,没有叶子。顶上长着一朵蓝色的小花,在雨中,徐徐摇晃,似乎呼叫。 不知坐了多久,当我回过神来,只觉头痛欲裂。一定是伤风了,幸亏我带了阿斯匹林。我从床下拿出热水瓶,想倒一杯水,可水已没了。我拿着热水瓶走下楼去。 仄仄的楼梯幽暗狭窄,整座屋子伟大而没有人气,雨声淅淅沥沥的象是能沁入石头深处,身上也情不自禁地以为冷。 我走进灶间,炉膛里另有焚烧。我看了看,柴禾却不多了,想烧水是不够的。我冲守雨帘,跑到柴房里,弯下腰,抱了捆麻秸。这时,突然有一阵恐怖,让我打了个寒噤,好象有人在偷窥着我,而我又看不见他。好象一桶冰水重新顶烧下,全身都冷了。 是二宝么? 我马上知道不是。由于我听到她在外面怪腔怪调地唱着什么。从柴房的窗口看出去,她正在廊下玩着泥巴,还不时向柴房里张望。我环视一下周围,说不出那种被偷窥的感受是在哪儿,周围堆着麻秸和稻草,不会有人的。可那种感受挥之不去,让我很不恬静。 我抱着柴禾出了门。二宝嘴里还在唱着什么,隔着一院春雨,那一带古旧的飞檐象一幅破了的水墨画。我伸手揉了揉太阳穴,让自己苏醒一下。简直,这幢房里没有第三小我私人了,表舅还没回来,他出去时带了蓑衣的,不用我送。而周围也没有值钱的器械,小偷也不会来惠顾吧,这应该只是我的多疑。 雨还在下,象湿润的蜘蛛网。虽然细小,但每一颗雨点照样可以感受获得。我仰起脸,却看不到一点雨。雨打在我脸上,一阵阵砭骨的寒意,但我没有快走,反倒想在院子里立一会儿。肩头上,雨水逐渐打湿了我的衣服,突然让我想到了小时刻那些恐慌万状的日子,每一天都云云。每一天都让我无比的伶仃,无比的无助。日子总是云云么?我有点想问自己。 我穿过院子,走进灶间。把麻秸拗断了扔进灶膛,火燃起来了。火光中,身上有了点暖意。我把一根麻秸又拗断了,想放进去,二宝的歌声飘了几句过来,听不清什么,也象雨。 突然,我愣住了手。她唱的,是那两句诗:“最是梦回呼不应,灯昏月落共凄神”!只管她唱得不清晰,却正是这两句。 火燃着,可是我身上,却越来越冷。 门开了。 门开了后,从外面飘进来一股白色的烟气。这些白烟比空气重,所在只在地上流动,象水一样。也许,是干冰吧?可表舅家里怎么会有干冰呢?我一定是在做梦。 我躺在床上,身上象压了万斤重物,没设施移动,只能用眼角的余光看着门。 门无声地开了。我看到了一小我私人。 一个女人。 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二宝,由于她比二宝高一些,走路也十分轻盈,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袍,但不象是睡袍,二宝也不象不睡袍的人。我看不清她的面目,只能看到一个轮廓,在床上看去,倒象是从水底看出来的。 她走动时,无声无息,白袍的下摆象水纹一样流动,看获得她腿的样子。 然而,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,倒象一部妖艳的鬼片。我一定是在做梦,我想。 你在做梦,你什么也看不到。 在心底,我以自己这么说。有时做了一场噩梦时,我就么对自己说。我想睁开眼,但发现无论我若何起劲也不能做到。 我怎么看到她的? 直到这时,我才发现我并没有做梦,我的眼睛本就是睁着的,看获得蚊帐的顶。这些老屋子没有天花板,因此常有灰尘落下来,蚊帐一年四序挂着,顶上铺着一层旧报纸遮挡灰尘。我可以看到透出酿成黄褐色的帐子,那张不知何年何月的报纸上的一幅传真照片,一些人在眉开眼笑地庆祝什么。 她走近了。象炎天中午看一张燃烧的纸片,看不到火苗,只能看到那条移动的焦痕。 更近了。 我瞥见了她的脸! 她的脸只管苍白,没有神色,但我一眼就认出了,她正是谁人常泛起在我梦中的女人! 她是谁? 我发现我的头脑杂乱成一片,身体也僵硬麻木。似乎是个梦,也许正是个梦吧,我无法让自己的身体动一下。是死了么? 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哭叫。象是一块石子投进了一潭死水,我一下子醒过来,身体也可以动了。可是没等我动,她已转身跑出了门。 这不是梦! 我只觉全身都冷意森森,毛骨悚然。床前,还留着一股白烟,窗外,雨不知什么时刻停了,透过窗板的裂缝,一钩残月冷冷地挂着,那朵蓝色的小花不时摆过,留下一个影子。 门外,有人奔跑的声音! 我披了件衣服,翻身下了床。踩在那白烟里,一阵透骨阴寒。我一把拉开虚掩着的门,跑到过道里。 夜色中,月光朦胧不明,但我照样瞥见了一个白色的影子一闪,进了柴房。我扑在栏杆上,高声喊着:“是谁?我瞥见你了!” 二宝的哭声大了起来。月色如水,如冰,如石,如烟,也如刀。 我冲下楼,掉臂一切地向柴房跑去,耳边,风声象吃吃的笑语,又象恶毒的挖苦。我冲到柴房门口,猛地拉开门。 通到后院的门开着,一院蔷薇,开得妖异。残月如钩,冷冷地照着每一朵盛开的花,岂论是红的照样黄的、白的,同样带着狰狞。 进来吧。 象是蛊惑,有一个声音在我的心内情细地说着。 进来吧,我的嘴唇甜如蜜。你守候什么呢? 没有风,但叶片都在逐步发抖,象叹息。我压了压心底涌起的恐惧,捉住了那扇门的门框。 一只手捉住了我的肩。 是表舅。 他的脸苍白得吓人。他抓着我,眼里,充满了焦虑和恐慌。 “那是谁?”我挣开他的手,那条被蔷薇湮没的小道上,叶片和花朵仍在摇晃。 “是她!”表舅的手抱住了头,“我妻子。” “她为什么要住在那幢小木屋里?那里是人呆的么?” 表舅抬起头,他的眼里,泪水再也抑制不住,流了出来。 “是的,她不是人。” 我无法形容那时我的脸上是种什么神色。也许,不是我疯了,就是表舅疯了,或者我们都疯了。我高声说:“她会走,会跑,不是人,岂非是具遗体么?” 表舅溘然高声吼道:“是的,她是具遗体!你懂了么?她是具遗体!” 我的全身都冷得象要结冰。死后,传来脚步声,以及一个微弱的哭声。我回过头,是二宝,她的脸上全是泪水,站在柴房门口。在她的眼里,除了弱智人特有的麻木,另有着一种说不清的痛苦。 表舅挥了挥手,道:“二宝,快去睡觉。” 他掩上了门,柴房里,登时暗了下来。不知是幻觉照样真实,我好象听到一小我私人的哭叫。 “那是我妻子,你也该叫她表舅妈的。” 表舅垂下头,他的话语中,有着无限的痛苦。我看着他,说:“告诉我,把一切都告诉我吧。” “好吧。”他抬起头,“你也许不会知道,就算知道也不会信托,我现在只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佬,可是,我曾经是╳╳医大的高材生。” 我小小地吃了一惊:“我听我妈说过,五十年月家里出过一个大学生,差点要到苏联留学,厥后由于出生有问题,去不成了。” 表舅苦笑着,看了看我,道:“你也知道?我还以为没人知道了。反右那阵子,我被打成右派,那时,你的表舅妈照样我的同砚,比我低一届,她帮我说了两句话,效果她也成了右派。结业的时刻,我们都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省份去了。一直到六九年,我们才结了婚。不由于其余,由于那时的兵团政委看上了你表舅妈,而她也跟我一样,是个田主子女。唉,那些事,不说也罢。” 我叹了口吻。还好,我妈这一支败得早,划分成份时成了下中农,否则,我一出生就是个小黑崽子了。 表舅站在柴房门口,天最先阴了下来,似乎要下雨。准时间,也快天亮了吧,可现在反倒更暗了些。 “娶亲后,由于我们都是右派,兵团遣散后只能回家务农。那时你的曾外祖母,我奶奶还在,一面种种地,一边照料照料她,日子也过得不算坏。那时你妈带着你也来住过几年,由于地方偏,革委会也没来找穷苦。” “厥后太太死了。”我看看过面的屋子,楼上,走廊的栏杆也只是些淡淡的虚影,轻轻的,象烟凝成。“我还记得,不少人来这儿,我也回一趟。” 他点颔首,道:“那是过了几年的事了,你妈已经带你回去了。那是最后一次一人人子团圆,厥后再也没人来过了。” “厥后呢?” 天更暗了,月亮已经被云遮了,空气也冰凉得干燥。我打了个寒战,但也没有想到回房里去。 “厥后?她得了一场大病。原本也不是什么大病,只是由于下雨时受了点凉,伤风引起的。要是有点阿斯匹林,马上就会好,可是她一最先没说,当我察觉时已经很严重了,约莫已经生长成肺炎了。我把她带到医院里,可那些医生却说我们是田主加右派,竟然不开药。活该的,若是那时我手里有把刀,我想我会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的。我赶回乡里,在光脚医生那里只找到几支过时的青霉素。明知道没什么用,我照样给她打了一针。 “回抵家里,她的烧更严重了。我发狂一样翻检着家里仅剩的医书,想给她找一副草药。这时,我真恨自己学的是西医而不是中医。我大着胆子给她凑了一副方子,也只是些手头能搞到的草药,熬好了给她喝下去,她似乎镇静了些,可是我知道,那毫无用处,基本没用。” “她死了么?” 他痛苦地抱住头:“有时我真希望我没给她喝下那副药,也许她死了会更好一点。那天,我以为她的身体在一点点变冷,嘴唇也失去了血色,” 我毛骨悚然地听到他念出了两句诗:“最是梦回呼不应,灯昏月落共凄神。”我大着胆子,说:“表舅,这两句诗是什么?” “不知道。她死前,溘然精神好了许多,说是她最喜欢这两句诗。她的话很清晰,但我听了却只以为毛骨悚然。我看着她的笑容淡去,象凝固在脸上,嘴唇也逐渐酿成了灰色。我希望有一个神,纵然让我马上死了也算,可是,她的身体照样冷了。 “我摸着她的身体。她的身体已经最先坚硬,象冰。天黑了下来,大宝已经吓得睡着了。那时,我也着实有点疯了吧,我想一定不会正常的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醒过来时,那一天,也是下雨,我听着外面的雨点不停敲着门,好几回我都以为她只是出门去了,回来得晚了,可每一次打开门,门外只有风,吹进几颗雨点。我看着她躺在桌上,心里也只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心酸。不行,我不能让她死。我对自己说,可我能做的,又是什么?什么也做不了,只是呆呆地坐着。这时,我才想起,要是大宝醒来,发现他妈妈还躺在桌上,他会怎么想?只有这时,我的脑子才最先有了一点正常的头脑。我抱起了她。她的遗体好象比在世时更重。我不想让她的遗体埋进泥里,被虫子啃吃成一块烂肉。我不能救活她,至少,我可以让她的样子永远保留下来。 “谁人园子照样很早的时刻留下来的。那时内里只养了些鸡鸭,另有一间放杂物的木屋。我把她抱到后院里,天很黑。我最先磨一把菜刀。呵呵,也许你想不出我要干什么,我只是想,我没有药,不能保留她的遗体,纵然有福尔马林或者酒精,她浸泡在内里也会走样的。我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她,纵然她没有生命,我也要让她的优美永远不会逝去。” 我只觉背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。表舅说的那时他有点不正常,我绝对信托,我看到他现在的眼神也带了几分疯狂。 “天啊,你要……” 他笑了,象哭一样的笑:“是,我要剥下她的皮,把她制成标本。在医学院里,我学过动物标本制作法,我有信心让她的样子永远留下来。我看了看菜刀,已经磨得象一片正在融化的冰,我用手指试了试刀刃,我的手指上一下被割开了条口子,血流下来,一手都是。可是,我一点也没以为疼。我抓着刀,走到她身边。她放在了一块寿材上,那是你外公以前为自己准备的,可是他一走没回来,一直就扔那儿了,呵呵。她躺在那儿的样子,好象睡着了,顽皮地想要我叫醒她。我拉开她的衣服,让她的身体裸露在外面。烛光下,她的皮肤已经发青。我知道,若是再等下去,即将形成尸斑,那么制成的标本就会有瑕疵。我把刀放在她肋下。你知道,剥制对照大型动物的皮时,刀口开在腋下是对整张皮肤损坏最少的设施。” 他一定瞥见了我在发抖,笑了:“放心,我并没有下刀。事实上,我的刀已经割破了她的一小块皮肤,但我发现在皮肤下,渗透了一些血液。那血液并不多,但确实是新鲜的血液,不是凝固的血块。我吃了一惊,由于她死去已经好几个小时了,身体内部可能还会有点未凝固的血,但真皮层里的毛细管里,一定早凝固了。现在她的皮肤破了还能流血,那么,她是假死! “意识到这一点,我象疯了一样跪在地上,向天主、佛祖、穆圣、湿婆、玉皇大帝,横竖我知道的什么神示意谢谢。我也求他们不要让我空欢喜一场,由于假死并纷歧定会苏醒,许多时刻由于心力衰竭,假死生长成真死。我祈祷了一番,但实在我也知道,这多数是我配的那副药起作用了。我拉过一张破椅子,捉住她的手,看着她的脸。果真,她的眼皮在极其细微地哆嗦。你知道,一小我私人有知觉,眼球会动的。一小我私人假睡,你只要看他的眼皮在动就知道他在装假。我看着她的眼皮约莫五六分钟后极其细微地一跳,每一跳我的心脏也都要遭受一次伟大的袭击。每一次瞥见她的眼皮一跳,我就想着,她会一下坐起来,也许,瞥见她光着身子,腋下另有一小条伤口,可能会怪我的。我伏在她胸口,想听到她心跳的声音。可是新鲜,她的心脏并没有跳动,或者,跳动得极其微弱吧。我抓过蜡烛,在烛光下,她有皮肤最先了一种新鲜的转变。在皮肤里层,好象有什么在流动,我看着有一道阴影流到脖子,又到了胸口,然后转到背部。我知道,那一定是血液。现在她的血液最先自行流动,也就是说,她很有可能会马上苏醒的。我站起身,可马上也明了了,跪下来祈祷只是虚耗时间,我必须辅助她尽快苏醒过来。我冲到灶间,用我生平最快的速率生起了火,把锅子里倒了水,又挖了斗米倒进去。当她醒过来时,一碗热粥是最好的滋补品。 “我心不在焉地烧着水,水却慢吞吞地只是有点温热。纵然在灶台边,我的心也到了她那儿了。溘然,在耳朵里,我好象听到了她在呻吟。我冲到后院,果真,她躺在棺材板上,赤裸的身体上,象有什么在动,但看不出来。一块儿她的嘴唇一下子变得红润欲滴,一会儿又干裂得好象晒干的土皮一样翻卷出来。我捉住了她的手,她的手照样冰凉,但我感受获得,在她的掌心最先有点湿润。那是一点汗,只管很少,少得象快干的露珠,可我知道,这意味着她会醒过来。” “我伸心摸了摸她的额头,她的额上也最先有汗了。可是,她的身体却一直僵破着不会动,心脏也一直没有跳动。我不知道其中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,我没有药,没有仪器,连一支水银温度计也没有。可是,我想我一定要救活她,纵然丢掉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。 “我摸了摸她的嘴唇,这时,她的嘴唇已经很干了,摸上去象一块粗拙的纱布。而这时,我瞥见她的眼睛动了一下,好象要张开来,却又张不开。我吃了一惊,抱住她的手,高声叫着她的名字,可是,她基本听不到我的声音,照样石头一样,一动不动。 “这时,我瞥见了她的嘴唇上,依有数一点笑意。很淡,但却最先柔和起来。那就象一块扔进火里的冰,你看着它一下子从有楞有角变得圆润,却不知道它是怎样一个历程。那时也一样,我不知道她从什么时最先有了点笑意,而嘴唇,又最先红润了。 “我抱住她的头,想吻一下她,但她的嘴唇照样干硬冰凉,和看上去的样子完全差异。我凑近了看,原来那点红润是血。一定是适才我摸她的嘴唇时,伤口裂开了,血流到了她唇上。而边上只是一支忽明忽暗的蜡烛,我没有看清。 “这时,象有一个霹雳打下,我一下明了我该怎么做了。我把手指上的伤口往双方拉了拉,一些血又渗了出来。我把手指塞进她的嘴唇,最先,象塞进一块冰里,可逐渐的,好象这块冰在融化,我感应她在吸吮。而随着她的吸吮,她眼皮也最先跳动得更急,而神色也最先红润起来。我从她嘴里拔脱手指,抓起适才扔在一边的刀,在手指上又划了几下。马上,我的手指象张开了几张嘴,红宝石一样的血从伤口挤出来。我把手指伸进她嘴里,她的吸吮更有力了,而她身上,也最先变得有点暗。我知道,在皮肤下,她的血液已经流动得更急了。她的吸吮让我的手指感应有点痒苏苏的,基本没有以为疼。我抽脱手指,这根手指上,伤口已经被吸得发白,没有血了。我又在另一根手指上割了几刀,现伸进她嘴里。我想,就算我把我全身的血液都给她,我也不痛恨。 “天色有点亮了。她的身体已经和一个正凡人没什么差异,只是少了点血色。我听了听她的胸口,可是,她的心脏照样没一点跳动。我又失望又伤心,这时,她却一下坐了起来。在棺材盖上,她赤裸着,象一个女妖一样,坐了起来,睁开眼……” 表舅一下蹲在地上,两手抱住头。这时,我才注重到,他的两条手臂上,横七竖八的都是些伤口。象被什么猛击了一下,我醒悟到什么,但又象有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我的喉咙,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也许,那就是表舅为什么离群索居这么多年的缘故原由吧。 天还在下雨,雨下得细细密密的。二宝还在楼上哭泣,我看看柴房,在黎明前的漆黑中,更象是魔域而非人世。 “表舅,”我逐步地说,“打扰了你那么久,我也该走了。” “好吧。”他点颔首,“你也该早点出门,车子很少的。” “好的。” 我不敢跟表舅多说什么,抓了我的包裹,逃也似地冒雨出门。走出了十来步远,我转头望了望,那幢大屋子昏暗得象烟。在楼上,也许是我看错了吧,一定是我的神经虚弱又犯了,依有数一个白色的身影站在我住过的那间屋子的窗前。 到了镇上,天已经大亮了,及早集的人正准备回家。我找了个小店,在楼下的大间要了点豆乳油条。不是没钱到楼上买个清静,而是我有点畏惧。这时,我才以为周围的人气是那么温暖,那些汗臭和湿润也并不太憎恶。 等着送上来的时刻,在楼梯口,我瞥见有两个蒲篓。蒲篓上用浓墨写着大宝的名字。大宝也在这儿么? 跑堂的把器械端上来了。我指了指那堆器械,说:“那是谁的?” 跑堂的看了看,说:“可怜,那是个小贩的。他回老家里打点一下,器械寄存在这儿,回来时跟两个混混吵嘴,一刀子就送了命了。” 大宝死了?我的心头一阵凄楚。表舅也许还不知道这事吧?也许,也就是那天大宝回家一趟后,回来就死的。我记得我来时这小镇上就出过这么一趟事,看来,这么个小地方,治安也很差。 我说:“是啊。他家里人还不知道他死了。穷苦你告诉一下他家里人吧,就在离这儿十几里地。” 跑堂的笑了:“同志,他家里人早死绝了,一个也不剩,他亲口跟我说的。” 也许大宝也有点知道内情吧?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家里有这么一件事。我不再多问了,顾自吃着。吃完了,会了钞,我准备及早上的远程。可是,心里却好象总有点什么搁着,我想再问一下谁人跑堂的,可他正忙上忙下,卖完器械的乡下人都来品茗了,楼上楼下都是人。好容易,等他空了一点,我追上他,道:“对不起,我还想问一下,谁人小贩死了几天了?” “很多多少天了。”他肩头搭了块毛巾,手里提着把大铜壶,正准备上楼。我又追问了一句:“到底是哪一天?” 跑堂的想了想,溘然冲楼上喊:“喂,严家三,你记得大宝被小猪头捅死的那天是几号么?” 楼上一小我私人瓮声瓮气地说:“那天是星期五,不是影戏船来的那天么?他们就是为买票争起来的。” “哦。”跑堂的回过头来,跟我说了一个日子,没有再理我,顾自上楼去了。他不知道,我全身都象浸在了冰水里。 那天,正是我来的日子。,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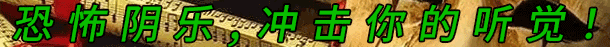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