灵魂飞翔(一) 这一天夜里突然停电了,小镇漆黑一片。 男女老小的狗一齐狂吠起来。 有杂乱的脚步跑动声,有大人寻觅自家孩子的呼啼声,尚有手电筒的光,在夜空中晃来晃去…… 有电话的人家纷纷向变电所询问,可是一直占线,打不通。 一些人家点上了蜡烛,烛光微弱。整个小镇似乎半梦半醒。 张古原本要写一份主要讲述的,他是镇政府的秘书,明天要交上去。可是,电脑用不成了,他特着急。 他走出门,计划去变电所问问。 今天在变电所值班的正巧是他的同伙冯鲸。他比张古大几岁,他俩都是网虫。 三个邻人女人在院子里纳凉。没有电,在屋子里没意思。 她们和张古开顽笑:“小伙子,咱们17排房只剩下你一个男子了,天这么黑,你要珍爱我们,可不能逃走啊!” 张古笑道:“我还指望几个嫂子珍爱我呢!” 小镇都是连脊屋子,一排五家。张古住的这排屋子,位于小镇最北端,编号第十七排。房后面,就是宽阔的庄稼地了。最近一段日子,除了张古,其他几家的男子偏巧都不在家。 变电所在小镇田野,约莫一公里。张古跑步很快就到了。 他进了值班室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,问:“冯鲸,怎么搞的?” 冯鲸说:“我也不知道,我一直给县里打电话,占线,一直打不通。 “今晚能来电吗?” “那可说禁绝了。” 张古骂起来。 冯鲸还在一遍一各处拨电话。 张古说:“看来,我的讲述只有明天到单元写了。”说完,他起身朝外走。 他走到门口的时刻,冯鲸突然在后面问他:“张古,你说,三减一即是几?” 张古回过头,冯鲸正认真地看着他,守候他回覆。张古以为冯鲸的神情似乎有点和平时纷歧样。他有点莫名其妙:“你说呢?” 冯鲸:“我固然知道了。现在我问你呢。” 张古一本正经地算了算,然后说:“我算不出来。” 冯鲸一下笑出来。 张古:“你到底要干什么?” 冯鲸:“是这样的——我想在互连网上起个名字,就叫——三减一即是几。起名之前,我想对十小我私人问这个算术题,若是十小我私人都脱口而出,那就说明这个名字毫无意见意义,我就不叫它了。你是我问的第一小我私人,第一小我私人就告诉我算不出来,再不用问了,我就叫这个名字了。” 张古耐心地听冯鲸说完,说了句:“真无聊。”转身走了。 到镇里尚有一段路。 天很黑,双方是田野,没有一小我私人。 张古戴着随身听走在路上,他把音乐的声音调得很大。 ——我告戒你,这个天下不平安,你要时刻保证视觉、听觉、肤觉的敏捷,若是有什么情形突发,你做出的反映才会更准确。 张古还没有女同伙,他这个岁数最大的嗜好就是听音乐,摇滚乐,美国谁人死去的猫王,震耳欲聋。 突然,他望见黑漆黑路边有一团器械隐约在动。他停下来,仔细一看,竟是一个小小的婴儿。 张古吓了一跳。 音乐占有了他的耳朵,他什么都听不见。他手忙脚乱地把随身听关了。 谁人婴儿坐在那里,没有哭,他仰面看着张古,呜呜咿咿地吐着儿语。 张古凑近他的脸,仔仔细细地看。 是个男孩,约莫有1岁左右,光着腚。 忠实讲,这个男婴长得很丑,窄窄的额头,眼睛出奇地大,鼻子瘪瘪的,头发又细又黄……重新到脚脏兮兮。 张古四下看了看,没有大人,只有这个男婴。他俯下身,问:“你妈妈呢?” 谁人男婴仍然呜呜咿咿地吐着儿语,显然还不会语言。 张古犯愁地左顾右盼,大呼起来:“哎,谁的孩子?这是谁的孩子!” 空旷的野外,风很大,没有一小我私人影。 张古想把这个男婴抱回家,可是怙恃不在,到满洲里姐姐家去了,一年都不会回来。自己又没有娶亲,怎么养他呀? 他想来想去,没设施,只能回去向镇里人报信,看看有没有人把这个男婴收养。 他狠了狠心,扔下这个男婴,快步走了。 走出几步,他转头,望见谁人婴儿在黑漆黑悄悄看着他,那眼神有点庞大。他莫名其妙地主要起来,加速了脚步…… 几个邻人女人还在院子里谈天。 张古停在院门口,对她们说:“我在田野望见了一个孩子,不知道谁家的,没人管。” 李太太对另两个女人说:“有这样的事?走,咱们看看去!” 她老公叫李麻,是屠宰厂的屠夫,长得五大三粗。稀奇要交接,他有一把杀猪刀,钢口稀奇好,是他祖上传下来的,听说那把杀猪刀削骨如泥,他就靠这把刀用饭。最近他到外县收猪,离家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李太太是那种心广体胖的女人,异常善良。 卞太太问张古:“那孩子在什么地方?” 张古说:“就在路边,去变电所的路边。” 慕容太太一边站起身一边忿忿地说:“现在有一些怙恃真狠心,自己的骨血就舍得扔掉。前几天,我看电视上报道,有一个恶毒的母亲……” 慕容太太家里正好有一个不到1岁的女孩,这时刻的女人最母性,柔肠似水,哪怕一个不相关的孩子受苦都市刺痛她的心。 几个女人一起去了。 张古回抵家,随手去开灯,没亮,他蓦地想起停电了。 屋子里一片漆黑,他摸黑躺在了床上。 想起今夜的事情,他以为有点奇巧:平时小镇很少停电,今夜偏偏就停了,而且他又望见了谁人莫名其妙的男婴——似乎今夜停电就是为了掩护这个男婴泛起似的。 尚有,遇见谁人男婴之前,冯鲸似乎中邪了,竟然神经兮兮地问他三减一即是几。 张古以为这个算术题不祥瑞。 外面,那些狗都不叫了,只剩下一条狗在张古的门外叫,那声音很伶仃。 家里只剩下他一小我私人。 这趟连脊屋子就剩下他一个男子。 他以为这屋子空荡荡。 (二)三个女人果真把谁人男婴抱了回来。她们商议了一下,很快形成了一个约定:人人轮流收养这个1岁的男婴,每家一个月。若是孩子的怙恃找来,随时把孩子璧还。若是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,他们要配合抚育他到18岁。这趟连脊屋子共五家,除了张古和那三个盛意的太太,尚有一家,那是一个未亡人。她叫连类,是小镇的头号尤物。连类是从外地嫁到小镇来的,不善言谈。她丈夫死许多年了。一根绳子,挂在房梁上,吊死了,舌头吐多长。提及来,他死得稀奇不值得,似乎没什么大事,只是和连类拌了几句嘴。今后,人人更无法知道连类的根底了。丈夫死后,连类竟然没有回外家,也没有再嫁,她一小我私人留在绝伦帝小镇上,一直守着寡。虽然小镇很偏僻,然则这里的人很开明,他们都希望连类能够再找一个好男子,一个女人确实不容易,而且她还那样年轻。可是,人人没有和连类谈心的时机,由于她从反面人人来往,挺封锁的。她更反面17排房的邻人们来往,和17排房的几个女人有时走路遇见,只是简朴打个招呼,从不闲聊。她家挨着路,于是,她开了一个巴掌大的服装店,挣不了若干钱,仅仅是生活而已。几个女人把那男婴抱回来之后,李太太把连类叫出来了。她对连类说了她们几小我私人的想法,问她参不加入她们的约定。连类似乎极其倾轧这个婴儿,她看都不看他一眼,连连说:“不不不,我不想收养他。”李太太笑着说:“那好吧,以后我们是他妈妈,你就是他阿姨。”然后,连类低头就走了。她始终没有看谁人男婴一眼。直肚直肠的李太太第一个做这个男婴的母亲。男婴的衣服,名字,生辰八字,什么都没有带来,赤裸裸一个婴儿身。说他1岁,没有任何依据,仅仅是从他身体的巨细估量。若是是正常的孩子,这么大已经会说一些话了,可是他不会。他一直愣愣地看着眼前这几个生疏的女人,似乎很恐慌。李太太把他抱回家,给他煮了一碗米粥,还拌进了蔬菜末和精肉丁。他吃的时刻,把肉都吐出来,把米粥和菜都吃光了,之后,还呜呜咿咿地伸手要。李太太很喜悦,她知道,只要孩子要吃的就没什么大偏差。接着,她又给他冲了一杯牛奶。她数了数,这个男婴上下总共长了8颗牙。李麻的儿子4岁了,叫熊熊。他认真地问妈妈:“你为什么给他用饭?他也是你儿子吗?”李太太对他说:“熊熊,从今天起,他就是你弟弟,你不许欺凌他。”熊熊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丑弟弟,他不情愿地说:“我不要他当弟弟。”吃饱了,男婴的情绪似乎很多多少了,蹒跚着爬上床,去抓熊熊的玩具。熊熊高声说:“别动,那是我的!”李太太严肃地对熊熊说:“你这样就纰谬了。这个孩子比你小,他没有妈妈,没有玩具,多可怜。你应该尊崇他。”熊熊的眼神仍然有敌意。谁人男婴抓起熊熊的一个电动汽车玩起来。熊熊没设施,就把谁人电动汽车留给了男婴,把另外的玩具都抱走了,放到了其余屋子里。李太太叹口吻,温柔地对谁人男婴说:“瑰宝,你玩吧,玩够了妈妈给你换。”第二天一早,卞太太和慕容太太就来了。卞太太给男婴送来了几套小衣裤。慕容太太给男婴送来一只奶瓶,尚有几袋奶粉——她家这类物品太多了,迢迢基本用不完。李太太问卞太太:“你又没有小孩,怎么有这些小衣裤?”卞太太说:“都是我亲戚家的小孩穿过的旧衣服。”男婴见人多了,喜悦起来,呜呜咿咿地叫,手舞足蹈。卞太太说:“咱得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?”李太太说:“是得起个名字。”然后,她对卞太太说:“你读过中专,你起吧。”卞太太说:“随便叫一个吧,不就是个名字吗?就叫叉吧。台甫以后再说。说禁绝哪天人家怙恃找来呢。”“好,就叫叉吧。”李太太一把抱起谁人男婴,笑眯眯地逗他:“叉!叉!叉!——”几个家庭主妇在一起谈天,说着说着话题就会越轨,开一些荤玩笑。慕容太太对李太太说:“你老公原本以为你很礼貌,可是过一些日子他回来,发现你把孩子都生下来了……”李太太说:“就算我出墙了,孩子也不能能长这么快呀!”慕容太太坏笑说:“鬼知道你什么时刻背着他做过了。”李太太:“冤啊,你看我家除了李麻尚有一个男子来过吗?”慕容太太:“今早上我还望见有一个卡车司机进来了呢!”李太太:“那是连类家的同伙,他的卡车水箱漏了,来讨一桶水。他原本是去连类家的,连类家没有人。”卞太太凑热闹:“他是来讨水,然则干了什么就欠好说喽。”李太太:“胡扯,他5分钟就出去了。”慕容太太赞叹:“嗨,你们的动作挺快啊!”李太太:“你们这两个长舌妇,一会儿就被你们弄成真的啦!”卞太太和慕容太太就开心大笑。李太太说:“说真的,谁人司机是个挺不错的人,他说,明天上午还途经这里,去城里拉木头,下昼返回来。咱们搭他的车去城里转转好欠好?”卞太太最寥寂了,她老公是个生意人,一年四序在外面跑,留下她一小我私人在家独守空帏。她说:“好哇,我早想买几件衣服了。”慕容太太犹豫了:“可是,我家迢迢……”李太太说:“放你婆婆家呗。”第二天早上,李太太给两个孩子吃完饭,对熊熊说:“今天你照看叉,妈妈去赶集。别让他摸电线,别让他玩火。还要记着,你和他都不能出去,更不能到井边玩。饿了,有饼干和牛奶。妈妈下昼就回来。”熊熊懂事地址着头。那辆卡车来了,几个女人说谈笑笑上了车,走了。这一天,她们在城里玩得很开心。她们买的一堆器械里,除了有一些婴孩用品,剩下的就是一些在男子看来完全莫名其妙的器械,发夹啦,戒指啦,丝袜啦,口红啦,皮包啦……她们返回来的时刻,车在路上出了点故障,她们天黑才抵家。虽然熊熊这孩子挺妥靠,然则李太太照样有点郁闷,她急急遽赶回家。进了门,她望见熊熊在玩,他骑着小凳子当火车,“呜呜呜”地开。谁人叉老忠实实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她长舒一口吻。熊熊望见妈妈回来,立刻扑上来撒娇。叉似乎也熟悉她了,呜呜咿咿地叫。她和两个孩子亲近了一阵,马上下厨做饭。经由这一天磨合,熊熊对叉很多多少了,李太太闻声他对他语言的时刻,变得很柔和。孩子在一起玩玩就融洽了。李太太想。忙忙乎乎吃完了,已经很晚。李太太和两个孩子躺在炕上,关了灯。叉很快睡了。屋子里黑压压,只有靠窗子的地方有点白,那是微弱的月光。小镇的夜静极了。李太太抱着熊熊亲了一口,轻轻说:“熊熊真乖,都是大人了,可以照看弟弟了,妈妈明天给你买苹果。”熊熊说:“我还要巧克力。”李太太说:“尚有巧克力。”熊熊知足地枕着妈妈的臂弯闭上眼睛。过了一阵,熊熊溘然想起了什么,睁开眼,说:“妈妈,我闻声他语言了。”李太太愣了愣:“谁语言了?”熊熊指指旁边的叉:“他。”“他不会语言。”“我闻声他说了。”“说什么?”“他说,我掐死你。”“乱说!”“真的。中午我在床上看画册,他一小我私人在院子里玩,我闻声他骂了一句——我掐死你!”“他骂谁?”“院子里似乎来了一只大猫,我趴窗户朝外看,只望见一条尾巴就没了。”一个4岁孩子说的话怎么能信托呢?李太太笑了,她摸着熊熊的头说:“熊熊,不能编谎言啊,否则就会被狼吃掉的。睡吧。”熊熊就不再说了,往妈妈肩窝钻了钻,闭上眼睛,睡了。他以为那男婴有点不祥…… (三) 停电的缘故原由弄清晰了,或者说弄不清晰了——是电线断了,显著是被人剪断的,不知是谁搞的鬼。 电线断在小镇西边约莫一公里远的地方。铁柱在追查这件事。 铁柱是镇里的警员,一个鸡毛蒜皮什么都管的警员。只管他的智商天生有点低,可是 人人都很信托他,由于他专心致志为人民服务。 叉的怙恃一直没有泛起,他的身世照样一个深邃的谜。 过了一段时间,李太太发现一个问题:这个男婴从来不哭。他最爱干的事是看电视——才1岁的孩子,他最大的兴趣竟然是看电视!——若是大人有事情,把他放在沙发上,他可以一小我私人不哭不闹地看一天。什么节目都行。 最先的时刻,李太太以为他看什么节目都行。又过了一些日子,李太太逐渐发现了一点区别:他似乎更愿意看评书。就是那种穿长衫,拿折扇,桌子上放一块醒木——话说,这个叫李二愣的匪兵,别着匣子枪,来到倭瓜村,想弄几只肥鸡…… 他竟然喜欢评书! 电视里有时泛起评书,李太太感受他的眼睛就亮起来。 有一次,叉在看电视,熊熊在旁边玩水枪。一个卡通片完了之后,又来了评书,李太太随手又给他换了一个卡通片。叉一动不动继续看。过了一阵,李太太出去洗衣服。她有时进屋来,发现不知是谁又把电视换成了评书节目…… 这一天,叉有点发烧。晚上,李太太把他放在自己的被窝里,心疼地搂着他,他的身子很烫人。 熊熊有点委屈:“妈妈,不许你搂他睡!” 这孩子对叉已经很友好了,可是他对妈妈搂叉睡觉照样很嫉妒。 妈妈说:“弟弟病了。听话。” 熊熊就郁郁地睡了。 叉吃了药,也沉沉地睡了。 约莫是午夜,李太太做了一个梦,梦见谁人卡车司机又来了,他说他的卡车又渴了,异常热,需要水。 可是,李太太以为,似乎不是他的卡车渴了。 她说:你为什么不去找连类呢? 他说:她家锁着门。 然后,他突然干渴异常地抱住了李太太,他的身子像开了锅的汽车水箱,火一样平常烫人。 他摸她的奶子。 李太太以为十分好奇,十分含羞,十分主要,十分愧疚。 她无意间看到,谁人卡车司机的手小小的,白白的,嫩嫩的,像婴儿的手…… 这时刻,她猛地醒了,她发现谁人叉正用手抚摸她的奶子。 她眯缝着眼睛偷偷看他,他醒着,眼神和平时不太一样,很陶醉。 李太太以为,他这可能是恋母情结,摸着女人的奶子,他就回到了依偎在亲生母亲怀里的幸福时光…… 熊熊大了,很长时间没有孩子摸她的奶子了,她已经有点不习惯。她轻轻地把叉的手移开了。 她感受这个男婴摸她摸得很熟练,有点不像一个婴儿的动作。 这个直觉很罪行,也很恐怖。 五大三粗的李麻回来了。 他望见家里多了一个丑丑的男婴,很喜悦。 他先亲够了熊熊,又大咧咧地抱起叉。可是,叉对他却似乎有敌意,使劲地躲。 李太太说:“看你一身腥臭气,孩子不喜欢你。快去洗个澡。” 李麻哈哈地笑,把叉一下一下扔向高处。他的手很大,像两个簸箕,而叉在他的手里显得很小,像一只狗崽子。 这天晚上,熊熊睡在他自己的小床上,叉和李麻伉俪睡在炕上。 我曾经这样注解“孩子”一词:一种睡前在中央睡后在旁边的小器械。果真是这样。 李麻伉俪睡前把叉放在中央,逗他玩。玩了一阵,叉就困了,偎在李太太的胳膊弯里闭上了眼睛。李麻伉俪小声说着话,直到闻声叉发出稍微的呼噜声,才关了灯,迅速把他抱到了另一端。 久别赛新婚。 这对伉俪的身体都很棒,干柴猛火。 李麻抚摸着太太光秃秃的身子,脸憋得通红。她肥硕的身体像河堤一样高峻,双乳像熟透的西红柿一样色情。 李察的腹中翻腾着攀缘的盼望。 终于,他插入太太,最先爬坡,像一只粗笨的甲虫。 熊熊已经长大了,他压制着声音。 很快,太太的蜜穴就湿得一塌糊涂。 终于,他至高无上,满眼惊雷闪电,有一道闪电击中了他,他通体狂抖不已,玉液银浆喷射而出。 就在这时刻,一双眼睛跳进他的眼睛,他蓦地从最岑岭跌落下来。 是男婴。 是谁人莫名其妙泛起在自己家的男婴。 他在黑漆黑睁着双眼,一眨一眨,镇定地旁观着这对结实男女做爱的历程。 李太太感受有点纰谬头,轻声问他:“怎么了?” 李麻躺在炕上,阳具一下就软了,像棉花。他用下巴朝她死后的偏向示意了一下,低低地说:“谁人孩子醒着。” 李太太转过头,望见叉闭着眼睛。 李麻是个粗人,他很快就遗忘了这件事。 只管叉对他有点倾轧,李麻照样很喜欢他。他下班回来,经常给叉买一些好玩的器械,好比水枪和哨子之类。 闲暇时,他经常教叉语言:“爸爸!” 叉:“呜咿。” 李麻:“妈妈!” 叉:“呜咿。” 李麻:“爸爸!爸爸!” 叉:“呜咿。” 李麻:“妈妈!妈妈!” 叉:“呜咿。” 李麻再教,叉已经不耐性,挣脱李麻下地玩去了。 这一天晚上,天很阴,似乎要下雨。 李麻伉俪把熊熊和叉都哄睡之后,最先做爱。 这时刻已经快午夜了。屋子里漆黑一片,什么都看不见。李麻以为这样的环境才平安,才纵情。 他在太太身上像打夯一样运动。 又是在他迫近热潮的时刻,突然天空亮起一道闪电。李麻警醒地朝谁人男婴睡觉的偏向看了一眼,竟然又望见了那双黑亮的眼睛。 闪电一闪即逝。 那双眼睛一闪即逝。 李麻沸腾的血一下子就冷却了。他从太太身上翻下来,眼睛死死盯着谁人男婴睡觉的位置,突然把灯打开。 男婴睡得很香甜,像雪花一样镇静。他皱着眉想,岂非是自己发生了幻觉? 太太盖住眼睛问:“你看什么?” 李麻把灯关掉,陷入黑漆黑,他什么都没有说。(四)没有源头的哭 一个月后,这个男婴转到了卞太太家。 卞太太的老公还没有回来。她没有孩子,很寥寂,早盼着叉快点轮到自己家了。她提前买回了许多玩具。 把叉领回家的路上,她喜悦得蹦蹦跳跳,像个孩子。 进了家,她拿积木给叉玩。他摆了几回,都倒了,就不太感兴趣了。 卞太太收起积木,又递给他花皮球。 他笨笨地踢,踢禁绝。很快也不想玩了。 卞太太又拿出一本画册。 他翻起来。这次他专注的时间对照长。厥后,他把画册也扔到了一旁。 卞太太收起玩具,对他说:“叉,现在呢,我就是你的妈妈了,你要乖。你乖的话,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。” 晚上,卞太太按李太太嘱咐的那样,把便盆放在他的小床下,对他说:“午夜拉屎撒尿就用这个盆,记着了?” 叉似乎对卞太太家的电脑更感兴趣,他一次次跑到它的键盘前,伸出小手去摆弄。 天要黑的时刻,张古打字打累了,出门到院子里活起程体。 西天尚有一抹偷偷的血红。 他有时朝卞太太家的院子看了看。卞太太家没有开灯,可能是怕蚊子。在暮色中,他望见卞太太家黑压压的窗子里,有一双眼睛,正静默地看着自己。 他打个冷战,仔细看,竟是谁人男婴。 这眼神他见过一次,在停电的谁人夜里,他发现他又脱离他的时刻。他感受这眼神很庞大,不像是一个婴儿的眼神。 张古避开很庞大的眼神,继续伸臂弯腰踢腿。他想,也许是自己太多疑了。也许这一切都是由于他那时狠心脱离他,灵魂深处一直在不安…… 过一阵,张古又抬起头,望见谁人男婴仍然在黑压压的窗子里看着自己。 忠实说,在心里深处,张古对这个最早他发现的男婴有几分恐惧。 他尽可能回避他,可是,越回避越畏惧。那男婴的眼神,时时刻刻闪现在他眼前。 你越离一个眼神远你就越以为它飘忽。 你越离一颗心远你就越以为它叵测。 你越离一个黑影远你就越以为它有鬼气。 张古突然想靠近这个男婴。 他想,他对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儿,一定有一种误会。他要靠近他的哭哭笑笑,吃喝拉撒,摸清他的脾性,他的稚气。他要靠近一个真实的他,损坏这令他寝食难安的错觉。 可是,他没有勇气走近他,哪怕一次。 这天上午,张古到市场买菜。 回来时,他望见李太太和慕容太太在小镇汽车站等车。李太太跟他打招呼:“买这么多好吃的,招待老丈人呀?” 张古:“几个同伙要到我家来喝酒。你们去那里?” 李太太:“我们到城里去。” 张古把吃的喝的准备齐全了。下昼,他的几个同伙来了。其中有冯鲸。 喝酒时,张古问:“那天断电查清晰了吗?” 冯鲸说:“上哪儿查去!” 全镇只有张古一小我私人顽强地以为那天停电和男婴的泛起有关系。 同伙1问:“听说停电那天你们17排房捡了一个男婴?” 张古说:“是啊,怎么了?” 1说:“没什么。我只是听说,谁人男婴从来不哭,很少见。” 同伙2说:“不会是机械人吧?肚子里装着准时炸弹……” 同伙3说:“你说的似乎是一个手抄本里的情节,婴儿,准时炸弹,梅花党,南京长江大桥,什么什么的。” 张古打断他们:“别乱说。那是一个挺可怜的孩子。” 冯鲸说:“我想起了最近我在网上熟悉的一个网友,她叫永远的婴儿。” 张古的心一沉——永远的婴儿? 冯鲸:“是一个美眉。” 同伙2:“现在的女孩子都装嫩——你们瞧这名字。” 冯鲸:“她说,她之以是和我交同伙,是由于我的名字吸引了她。” 同伙1:“你叫什么?” 冯鲸:“三减一即是几。” 同伙3:“现在的男子都装高深——你们再瞧这名字!” 那天,人人喝了许多酒,唱起了歌。张古遗忘了男婴那憎恶的眼神,跟人人一起狂欢。他唱的是: 一言不发,岿然不动,灰土土傻站着我是个秦俑。没有哭泣,没有笑容,我生命的靠山是一派火红。 我想战天,我想斗地,我想抄起身伙砸出一堆笑剧。我想唱歌,我想吻你,我想一步登天住进月亮里。 琴心剑胆晶莹剔透,这辈子注定不长寿。哥哥请你慷慨一些借我一点酒,让我轰轰烈烈献个丑。姐姐请你放弃贞洁拉拉我的手,让这人世的花儿红个透……” 这是周德东的歌?——准确。否则我就不会花这么大篇幅写它了。 它是我开篇那段歌词的前部门,好欠好都请你原谅,写它的时刻我正处在装腔作势的岁数。着实很丢人——我的盒带只在一个地方脱销,那就是我的田园绝伦帝。那里的年轻人险些都市唱我的歌。 张古唱完,冯鲸说:“有一句歌词不祥瑞,应该该成——这辈子能活九十九。” ……闹到天黑之后,人人才散去。 张古酒量不小,然则,他也有了些许醉意。他躺在床上,想起自己刚刚唱的歌:这辈子注定不长寿……以为确实有点晦气。 他又想起了谁人男婴,心里有点虚。机械人? 突然,他醉眼朦胧地望见谁人男婴泛起在他的视野里!他打了个冷战,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。 卞太太抱着谁人男婴急急遽走进来。 卞太太说:“张古,请托,我婆婆心脏病犯了,正在抢救,我获得医院看护她。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!” 卞太太:“李太太和慕容太太都到城里去了。急死人!” 卞太太:“我明天一大早就回来。” 张古连连说:“没问题没问题。” 卞太太把孩子放下,又快快当当跑回去拿来一只奶瓶和一袋奶粉。 张古能说什么?说自己畏惧这个孩子? 人家收养这个男婴原本就是出于一颗善心,这男婴跟卞太太也没有任何关系,你张古收容一夜都不行?再说,老人病了,远亲不如近邻,这点忙都不帮?尚有,人家是女人,丈夫不在家,遇到难题,你一个小伙子能作壁上观? 从哪个角度讲,张古都没法推脱。以是只管他的心里很畏惧,可他照样说“没问题没问题”。 卞太太说:“谢谢了。”然后,她转身就走了。 屋里只剩下张古和谁人男婴。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放置。 很静。用一句老话形容就是: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。 男婴悄悄地坐在张古的床上。 张古看了他一眼。他正看张古。他和他第一次这样近地面劈面。 那男婴像眼科医生一样,仔仔细细地察看张古的左瞳孔。张古抖了一下,他立刻一定:这个婴儿的眼神决不是婴儿的眼神! 张古避开他的眼光,想说点什么,然则不知怎么说。 有两种语言方式。 一种方式是像对婴儿那样柔柔地说:“叉,乖乖,在叔叔这里不要闹,让叔叔抱着你……” 这种语气张古以为着实说不出口,由于他显著感应对方不是婴儿,他显著感应他的婴儿表皮里包藏着另一小我私人,包藏着一个邪恶的成年人。在只有男婴和张古的情形下,他的眼神似乎也不掩饰这一点。对于这个伟大的隐秘,他们在眼神里意会神通。 另一种方式是,张古爽性揭开面纱,直接和他谈判:“我知道你不是婴儿,你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,我想全天下的人都不会知道,我只想问你,你要干什么?” 然则,他的眼前究竟是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婴儿,若是他这样板着面貌向他发问,自己都感应恐怖…… 终于,张古逐步走到抽屉前,拿出一个口琴,递给叉,小声说:“叉,玩这个吧。”——最后他照样接纳了对婴儿语言的语气。这也证实了不管他何等一定自己的直觉,最终他对这个婴儿信托照样大于他的嫌疑。 叉不再看张古的左瞳孔,他接过口琴,摆弄一阵,并不会吹。 张古拿过来,吹了几下,又给他。 他学着吹,吹得杂乱无章。 这时刻,张古以为他又很像一个婴儿了。 过了一阵,张古在房间一角给他支了一张钢丝床——他不想和他一起睡。然后,张古试探着给他脱衣服,说:“太晚了,我们睡觉吧。” 他看了看张古,把口琴放下了。 可能是在两个妈妈那里训练出来了,他很听话,让张古脱了衣服,乖乖躺进了被窝。 睡前,张古在他的床下摆放了一些软垫,防止他午夜掉下来。 张古关了灯,屋子一下被漆黑淹没了。 外面,那条狗又在门外叫起来:“汪!汪!汪!”张古不知道那是谁家的狗。张古一次都没有见过它。只是,天天夜里它都到张古的门外叫。 他和他在统一间屋子里。 恐惧涌上张古的心头,他感应这个天下虚飘飘的,他想捉住一个牢固的器械,可是没有。 他屏住呼吸,严密关注着男婴的消息。男婴无声无息,像一个哑谜。 不知过了多久,门外那条狗住手了叫。屋里更镇静了。 张古全神贯注地听。 “啪……”隐约有木头干裂的声音;“唰,唰……”隐约有虫子走在墙壁上的声音;“咚咚咚……”隐约有老鼠跑动的声音;“呼,呼……”隐约有猪在圈里打呼噜的声音;“嗒……”隐约有水缸里冒泡的声音…… 张古十分疲劳,困意一阵阵袭来,他要合眼了。 突然,他在黑漆黑闻声了另一个声音,是谁人男婴发出的:呜呜咿咿。 这莫名其妙的儿语让张古无比恐惧,他的睡意一点都没有了。 谁人男婴很快又没有任何消息了,可是,也没有呼吸声,一片死寂。 张古屏住呼吸,继续聆听他。 过了良久,张古着实挺不住了,又合上了眼睛。 朦胧中,他闻声谁人男婴又最先发出了声音:呜呜咿咿哞哞,这次音节多了一些,有点像念经。 张古的心又一次被恐惧占有——若是男婴在梦中突然说出话来……想到这里,张古的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 他一动不敢动,把耳朵张得像饭盆那么大。 过了一阵,男婴又没声音了。 这时刻,已经是后午夜了。张古稀奇稀奇困,他的注重力稍微一放松,他的眼皮就黏黏地沾在一起,一下滑进了梦乡…… 模模糊糊中,他又听到谁人男婴发出了新鲜的声音。然则,他已经滑到梦乡的湖底,再没有漂浮上来……他做了一个梦,梦见谁人男婴逐步坐起来。他的心最先狂跳,想问他:你干什么?——可是,他怎么也发不作声音来,只好缩在被窝里,考察他的下一步行为。他以为男婴一定会走过来,可是没有,他摸起他的随身听,在黑漆黑摆弄着。突然,他哭起来。他的声音稀奇难听,像野猫在叫。 他不是从来不哭吗? 他不是从来不哭吗? 他不是从来不哭吗? 张古畏惧到了极点。他想悄悄跳下床,逃出去,可是身体却像被麻醉了一样,不接受大脑支配,一点也动不了…… 早上,张古醒来时,谁人男婴已经醒了,他躺在被窝里,手里拿着谁人口琴在玩,嘴里嘀咕着种种音节。 卞太太来了。她的眼睛很红,一看就是没睡觉。 “他哭了吗?”她进门就问。 “没有,挺乖的。”张古说。 “真是贫苦你了!” “哪的话。” 卞太太一边对张古讲医院的事情,一边麻利地给叉穿衣服。 她抱着男婴走出门的时刻,张古发现谁人男婴转头看了他的随身听一眼。 卞太太抱着谁人男婴走了。张古最先洗漱,又简朴吃了些早点,骑自行车出门去上班。 今天他听的照样周德东的歌:琴心剑胆晶莹剔透,这辈子注定不会长寿…… 突然,周德东的歌声酿成了一阵婴儿的哭声,那哭声怪僻而凄厉:“呜哇!——呜哇!——” 张古吓了一跳,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。 他清清晰楚地记着,这盒带是他六个月前在小镇音像店买的,他听过无数遍,没有任何问题。直到昨天下昼他还重新至尾听过一遍,并没有这个声音。 那么,是谁录上的? 只有一个可能:昨夜,谁人男婴在他睡熟之后,用随身听录下自己恐怖的哭声…… 他想,岂非昨夜自己做的谁人梦是真的?又一想,哭声这么逆耳,自己不能能不被惊醒啊!岂非是谁人男婴拿着他的随身听悄悄去屋外了? 张古毛骨悚然。 到了单元之后,他一天都心不在焉,镇长问他几件事他都答非所问。他用手翻来覆去地摆弄着那盘盒带,一直在想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若是不弄个水落石出,他会一直忐忑不安的。 终于,他决议对卞太太说出这件事。 他下班回家的时刻,望见卞太太正在院子里和谁人男婴玩秋千。他在院子外对卞太太喊:“嫂子,你来一下,我跟你说件事。” 他一边喊一边考察谁人男婴的眼神,没什么稀奇的反映,他玩得很专注。 卞太太过来了。 原本,张古想把他对谁人孩子的嫌疑都说出来,可话到嘴边又所有咽回去。他只是把随身听的事说了一遍,声音很低。 卞太太听后不解地问:“有这样的事?你嫌疑……” 张古有点欠美意思:“我只是想,是不是谁人孩子昨夜哭了,胡乱按了我的录音机,把哭声录进了盒带里……” “我们人人都没闻声这个孩子哭过一次,都在为这件事感应新鲜呢。基本不能能是他的哭声,一定是你自己搞错了。”卞太太说得很坚定。 她又弥补道:“一个1岁的孩子,午夜哭的时刻,胡乱抓起了录音机,又胡乱按下了录音键……哪有这么巧的事!” 张古干干地笑了笑,说:“那可能是我自己搞错了。” 这时刻,他的眼光越过卞太太的肩头看了谁人男婴一眼,他正在秋千上朝他看,那眼神说不清晰。 莫名其妙的婴儿哭声一直没有找到注释。张古只好把那段恐怖的声音洗掉了。哭声有十几分种,占用了两首歌的时间。之后,张古正常上班下班,日子无波无折。似乎没事了。然则,张古心中的阴影却没有消逝,它像乌云一样越来越厚重。 最后,张古把那恐怖的声音归罪于哪个同伙的开顽笑——他必须调动种种理由说服自己,否则怎么办呢? 着实,我们每小我私人都很会诱骗自己。一生中,我们不知诱骗过自己若干次,因此我们失掉了许多探寻真理的时机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,张古逐渐淡忘了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。 我们经常会遗忘一些事情,因此我们活得很幸福。但有时刻不完全是这样。在张古完全遗忘了这件事的时刻,一次他上班去,刚刚走出家门,戴上随身听,蓦地闻声一阵婴儿的笑声,那笑声极其怪僻,极其逆耳。他万分恐慌,猛地把随身听摘下摔到了地上! 他下意识地朝卞太太家看去,谁人孩子正在窗子里悄悄看着他…… 张古再一次断定: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!5、你卖头发吗? 张古以为,他时时处于某种危险中,只管他弄不清根底。而且,他以为整个小镇都笼罩在某种不祥之中——这真是先见之明。 他下定刻意,要把这一切弄个明晰。 今后,他变得像侦探一样敏感,仔细,富于推理性,充满想象力。 首先,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查清在谁人男婴泛起的日子,总共有三个从外地人到了绝伦帝小镇上。 一个是木匠社老张的侄女,她是一周后走的。 一个是县里来的人,公务,住在政府招待所里,他是三日后走了。 一个是江南来的老头,卖竹器的。他是绝伦帝小镇的老同伙了,每到这个季节他都来做生意,人人很喜欢他。他现在还没有走。 这几小我私人似乎都和谁人男婴牵涉不到一起,都被清扫了。 然则,必须认可张古的思绪是对的。而且,他做了大量仔细的事情。 这时刻的张古已经买了一顶鸭舌帽,戴上了一副黑墨镜,而且还叼上了一只烟斗。八小时势情之外,他就换上这身装束搞考察。 他不想让任何人认出他来。 这还不算,他走路的时刻,总是竖起衣领盖住脸,总是用鸭舌帽和墨镜严严实实地遮住眼睛…… 张古这个神秘的新形象在小镇的一个偏僻角落泛起了,他偷偷摸摸地走着,自己都以为不是自己了,却有人远远地跟他打招呼:“嗨,张古,你去那里呀?” 是小镇文化站的站长,她叫刘亚丽。她骑着摩托车。 ——真泄气。小镇太小了,相互太熟悉了。 张古尴尬地说:“我,我……” 刘亚丽终于没等到他的回覆,摩托车已经“突突突”地开远了。 厥后,张古注重到最近发生了一个不被人注重的事宜:小镇上莫名其妙泛起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太太。 她六十多岁了,脸上的皱纹很深刻,双手很粗拙,一看就是刻苦的人。 她第一次收的是铁柱家的废品,一些旧报纸和几个空酒瓶。她掏出钱来,都是皱巴巴的小毛票。 铁柱的母亲说:“不要钱了。” “那怎么行。” “废品,能值几个钱,你不来收我们也得扔掉。” “那谢谢了。” 对于小镇的住民来说,她是个外来人,不容易,人人都挺同情她。 厥后,谁家有了旧纸、废铁、破鞋、绳头什么的,就装在塑料袋里,摆在门口,等她拿走,到供销社卖掉。没有人要她钱。 张古悄悄跟踪过这个老太太,他觉察她总似乎心事重重,收废品三心二意。他嫌疑,收破烂仅仅是她的一个果然身份。 这天,张古又一次跟在老太太的死后。 她推着垃圾车朝前走,那车吱吱呀呀响。她走过一家又一家,拾起一个又一个废品袋。她的嘴里慢悠悠地喊着:“收破烂喽。” 一个孩子跑出来,送来两个酒瓶。老太太给了孩子几张小毛票,那孩子乐颠颠地装入口袋,跑开了——这是孩子惟一的正当收入,他们要用这些钱偷偷买爸爸妈妈不许买的器械。 然后她继续走。 到了17排房,她绕开了。 张古溘然想到,这个老太太从没有到17排房来收过废品。为什么? 张古一下就遐想到谁人男婴——她与谁人男婴有关系! 张古突然感动起来,他要叫住她,单刀直入问个明晰。她究竟是成年人,有什么话都可以谈,劈面锣劈面鼓。而谁人男婴,简直把张古酿成了聋子和哑巴。 张古语言了:“喂!请你站一下!” 谁人老太太逐步地站住,回过头来。 张古走已往,停在她的眼前。他第一次和她这么近,他把她看得清清晰楚。张古发现,不知是五官,照样神志,这个老太太竟和谁人男婴竟有点相似。 她直直地看着张古。 张古直言不讳地问:“你听说过17排房收养的谁人男婴吗?” 老太太的脸像木头一样毫无反映,她淡淡地说:“什么男婴?我不知道。” 然后,她不虚心地转过身去,推着垃圾车走了。走出几步,她又回过头来,突然问:“你为什么随着我?” 张古一下有点忙乱:“我……” 老太太:“你买废品吗?” 张古:“我不买。” 老太太返回来,一步步走近他:“那你卖废品吗?” 张古有点结巴了:“不,我没有。” 老太太停了停,轻轻地说:“你有的。”然后,她指了指垃圾车,内里有一堆乱蓬蓬的头发,人的头发,可能是在发廊收来的,裹着厚厚的灰尘。她说:“你看,我还收头发呢。” 张古确实好长时间没有剃头了,他的头发很长。他讪讪地说:“我没事儿卖什么头发呀?” 老太太叹了一口吻,说:“不卖就算了。”说完,她又走了。这次她再没有转头。 一阵风吹过,张古的长发飘动起来,他感应天灵盖发冷。他站在原地,一直看她推着垃圾车吱呀吱呀地走远…… 他在琢磨,这个老太太什么地方和谁人男婴长得像。 他在品味她的神色,以及她适才说的所有话。 这天夜里,张古做噩梦了。 黑漆黑,有一小我私人在他头顶转悠。他恐慌地坐起来:“谁!” 正是谁人老太太,她小声说:“嘘——别语言,是我。” 张古说:“你来干什么?” 她说:“我来收你的头发呀。” 张古果真望见她的手里拿着一把铰剪,闪闪发光。他说:“你滚开!” 她没有生气,低头从兜里掏出一叠一叠脏兮兮的小毛票,递向张古,说:“我把这些钱都给你。” 这时刻,她的老眼炯炯发光,上下端详张古,流着涎水说:“你的身上有许多值钱的器械,全身都是宝哇。” 接着,她神秘兮兮地说:“我除了收头发,还收指甲,还收眼珠,还收……”她朝窗外看看,加倍压低声音:“我还收心肝肺。” 张古已经吓得抖成一团:“你去屠宰厂吧,我不卖!” 她说:“猪鬃哪有你的头发好呀?” 他最先讨饶了:“你放过我吧……” 她耐心地说:“你不懂原理吗?秋天到了,我就要割你的麦子。指甲长了,我就要剪你的指甲……” 他惊慌地用被子死死蒙住头。 她轻轻掀开被子,说:“尚有一句呢——阳寿没了,我就要索你的命。” 然后,她轻轻按住张古的脑壳,最先剪。她的手法极其天真,一看就是这类手艺的权威。那把亮闪闪的剪子上下翻飞,从四周八方围剿张古。他傻傻地看着,身子一点都动不了。 “嚓嚓——”他的头发没了。 “嚓嚓——”他的眉毛没了。 “嚓嚓——”他的两只耳朵掉了。 “嚓嚓——”他的鼻子掉了。 “嚓嚓——”他的两只眼珠掉了。 “嚓嚓——”他的心肝肺都掉了。 他只剩下喉咙了,他竭尽全力地喊了一声:“救命啊!——” 那铰剪立刻又瞄准了他的喉咙……(未完待续),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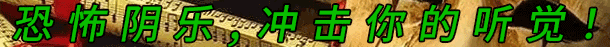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